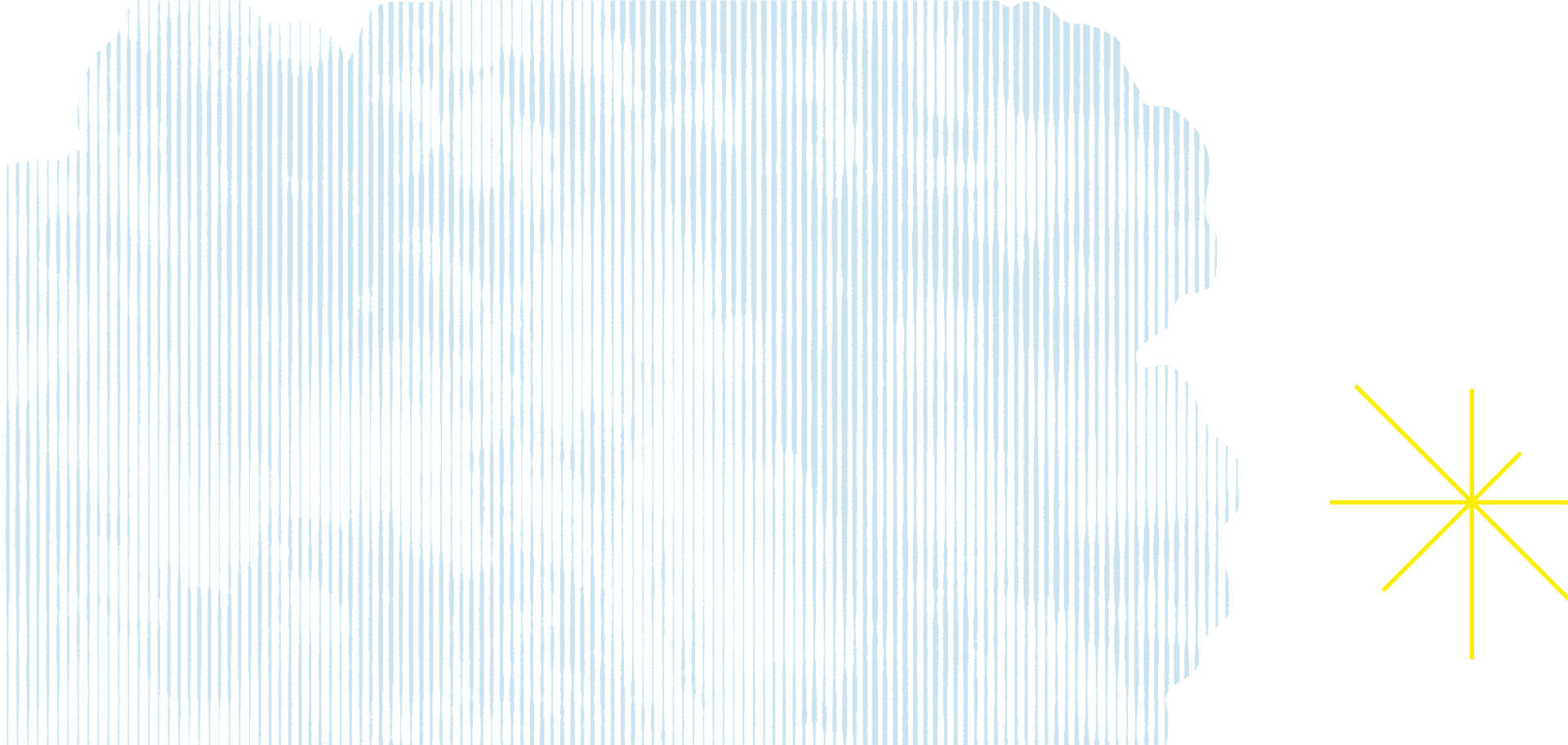部落格
2020.12.31
《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人物專訪II:戲劇的當下與未來
時 間|2020年10月05日(一)21:00
受訪者|栢優座座首許栢昂、仲首王辰驊
編 輯|沈佳燕
撰 文|莊馥嘉 (電影系四年級)
2019年,臺灣本土劇團栢優座的最新作品《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在新點子實驗劇場首次登上了舞台1。
2020年,栢優座將《大年初一》再一次帶到了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身為編導、同時飾演三子及趙雲的許栢昂在訪談中提到,自己原本打算將《大年初一》塵封起來。然而,經歷生活中的洗禮後,他期盼能重新以一個旁觀的角度審視這部作品。
.png) 戲劇與電影的語彙差異
戲劇與電影的語彙差異
談完了創作歷程中的感觸後,筆者問道導演是否喜歡看電影,電影是否對自己的創作有所影響。他認為「電影和戲劇是完全不一樣的,實在難以判斷一個電影演員是否具有『演戲』的能力。」導演補充原因:「電影的演員,是靠很多東西支撐起來的,可能是攝影機位置、角度、剪接或是道具。但是戲劇是完全以人為中心的,演員鮮少使用其他東西去輔助他們的表演。」這段話,讓筆者想起美國劇作家羅勃.愛德蒙.瓊斯 (Robert Edmond Jones) 也曾經在《戲劇性的想像力》(The Dramatic Imagination) 中提到,演員的表演能夠為一齣戲灌注靈魂與精神。戲劇中的表演是貫徹的、圓滿的,不會如電影因為劇情、剪接或是避免「出戲」而變得破碎。
導演沿著這個線索繼續延伸,「美國的電影演員,如果能夠在百老匯 (Broadway) 演出,便顯示他的演出能力是相當扎實的。只是這樣的觀念在臺灣很少見。臺灣並不認為好的演員一定要能夠演出戲劇。」對此,筆者在近年臺灣出品的電影及電視劇中,也看出了一些端倪。過去十年間,臺灣的主流影視注重演員的外型,多過於個人特質和表演技術,以至於許多影視作品流於平板及空洞。雖然近兩三年逐漸有更多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見你》、《鏡子森林》等影集,因演員的表演、引人入勝的劇情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及獎項肯定,但是其中的演員基本上仍不脫離亮麗姣好的外型,也因此忽略了演員在一部作品中所能發揮的最大價值及功能。
.jpg)
雖然認為戲劇和電影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導演並不否認,電影的某些特質仍對自己的作品產生了影響。「我個人很喜歡諾蘭 (Christopher Nolan) 或是昆汀.塔倫提諾 (Quentin Tarantino) 的電影。像是諾蘭的《記憶拼圖》(Memento, 2000),它的敘事方式不斷地顛覆前面的事實,也顛覆觀眾既定的想像。我在《大年初一》中也運用了這種時空穿插、非線性的敘事結構,而這就是電影所帶給我的影響。」
.png) 藝術在後疫情裡的發展
藝術在後疫情裡的發展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創作戲劇,沒有人傳承這項藝術,它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正在從事的戲劇創作,對於延續臺灣的文化傳統而言,是不能忽視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 (Karl Jarspers) 的意識形態 (Weltanschauung) 理論,曾闡釋了一種「腳下的地板被抽走」的不穩定狀態。這樣的狀態,正好對應了今年的疫情:2020年是動蕩不安的一年,新冠肺炎不僅帶走了許多的性命,也讓行動受限的人們感到不安。我們突然間失去生活的平衡,失去了對一切事物的確定性。賴以為生的、讓我們私以為這個世界的結構是穩定而恆久不變的意識形態遭到破壞。為因應政府對於大型活動的人數管制及防疫措施,許多藝文活動、展演及賽事也被迫取消,如每年春天的金馬奇幻影展在三月時宣布取消,連盛大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也確定將從明年二月延期至四月,著實為藝術工作者們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不過,不同於將疫情視為對工作的一種挑戰,導演反而看見疫情為文化產業所帶來的新契機與形式。雖然導演自嘲戲曲及現代戲劇在臺灣面臨「絕跡」的危機,卻也指出了這樣的藝術形式有其保存及延續下去的必要性。臺灣延續文化資產的政策雖尚有不足,但是透過發放藝fun券、補助藝文產業,政府讓藝術工作者們看到他們保存及支撐文化產業的努力。

.png) 戲劇在臺灣的未來
戲劇在臺灣的未來
透過這次的訪談,筆者得以與不同領域創作者談論創作、談論戲劇,不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導演的創作歷程及對於藝術、戲劇的看法,同時也激發了筆者對於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可能性的想像與思考。
至於對戲劇在臺灣的未來發展,導演又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呢?導演說道,對臺灣藝術的創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仍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形式,屬於臺灣的形式,並以這樣的形式講述屬於臺灣的故事。「臺灣歷史和文化背景提供了如此豐沛的創作元素,而栢優座創團十年以來始終不變的理念,更是從這些元素中汲取養分,創造屬於臺灣的藝術、屬於臺灣的戲劇。」
受訪者|栢優座座首許栢昂、仲首王辰驊
編 輯|沈佳燕
撰 文|莊馥嘉 (電影系四年級)
2019年,臺灣本土劇團栢優座的最新作品《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在新點子實驗劇場首次登上了舞台1。
2020年,栢優座將《大年初一》再一次帶到了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身為編導、同時飾演三子及趙雲的許栢昂在訪談中提到,自己原本打算將《大年初一》塵封起來。然而,經歷生活中的洗禮後,他期盼能重新以一個旁觀的角度審視這部作品。
.png) 戲劇與電影的語彙差異
戲劇與電影的語彙差異談完了創作歷程中的感觸後,筆者問道導演是否喜歡看電影,電影是否對自己的創作有所影響。他認為「電影和戲劇是完全不一樣的,實在難以判斷一個電影演員是否具有『演戲』的能力。」導演補充原因:「電影的演員,是靠很多東西支撐起來的,可能是攝影機位置、角度、剪接或是道具。但是戲劇是完全以人為中心的,演員鮮少使用其他東西去輔助他們的表演。」這段話,讓筆者想起美國劇作家羅勃.愛德蒙.瓊斯 (Robert Edmond Jones) 也曾經在《戲劇性的想像力》(The Dramatic Imagination) 中提到,演員的表演能夠為一齣戲灌注靈魂與精神。戲劇中的表演是貫徹的、圓滿的,不會如電影因為劇情、剪接或是避免「出戲」而變得破碎。
導演沿著這個線索繼續延伸,「美國的電影演員,如果能夠在百老匯 (Broadway) 演出,便顯示他的演出能力是相當扎實的。只是這樣的觀念在臺灣很少見。臺灣並不認為好的演員一定要能夠演出戲劇。」對此,筆者在近年臺灣出品的電影及電視劇中,也看出了一些端倪。過去十年間,臺灣的主流影視注重演員的外型,多過於個人特質和表演技術,以至於許多影視作品流於平板及空洞。雖然近兩三年逐漸有更多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見你》、《鏡子森林》等影集,因演員的表演、引人入勝的劇情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及獎項肯定,但是其中的演員基本上仍不脫離亮麗姣好的外型,也因此忽略了演員在一部作品中所能發揮的最大價值及功能。
.jpg)
昆汀.塔倫提諾示意圖片 取自網路資料 https://reurl.cc/7yEG69
雖然認為戲劇和電影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導演並不否認,電影的某些特質仍對自己的作品產生了影響。「我個人很喜歡諾蘭 (Christopher Nolan) 或是昆汀.塔倫提諾 (Quentin Tarantino) 的電影。像是諾蘭的《記憶拼圖》(Memento, 2000),它的敘事方式不斷地顛覆前面的事實,也顛覆觀眾既定的想像。我在《大年初一》中也運用了這種時空穿插、非線性的敘事結構,而這就是電影所帶給我的影響。」
.png) 藝術在後疫情裡的發展
藝術在後疫情裡的發展“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創作戲劇,沒有人傳承這項藝術,它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正在從事的戲劇創作,對於延續臺灣的文化傳統而言,是不能忽視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 (Karl Jarspers) 的意識形態 (Weltanschauung) 理論,曾闡釋了一種「腳下的地板被抽走」的不穩定狀態。這樣的狀態,正好對應了今年的疫情:2020年是動蕩不安的一年,新冠肺炎不僅帶走了許多的性命,也讓行動受限的人們感到不安。我們突然間失去生活的平衡,失去了對一切事物的確定性。賴以為生的、讓我們私以為這個世界的結構是穩定而恆久不變的意識形態遭到破壞。為因應政府對於大型活動的人數管制及防疫措施,許多藝文活動、展演及賽事也被迫取消,如每年春天的金馬奇幻影展在三月時宣布取消,連盛大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也確定將從明年二月延期至四月,著實為藝術工作者們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不過,不同於將疫情視為對工作的一種挑戰,導演反而看見疫情為文化產業所帶來的新契機與形式。雖然導演自嘲戲曲及現代戲劇在臺灣面臨「絕跡」的危機,卻也指出了這樣的藝術形式有其保存及延續下去的必要性。臺灣延續文化資產的政策雖尚有不足,但是透過發放藝fun券、補助藝文產業,政府讓藝術工作者們看到他們保存及支撐文化產業的努力。

栢優座彩排精彩片段 攝影游翔皓
.png) 戲劇在臺灣的未來
戲劇在臺灣的未來透過這次的訪談,筆者得以與不同領域創作者談論創作、談論戲劇,不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導演的創作歷程及對於藝術、戲劇的看法,同時也激發了筆者對於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可能性的想像與思考。
至於對戲劇在臺灣的未來發展,導演又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呢?導演說道,對臺灣藝術的創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仍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形式,屬於臺灣的形式,並以這樣的形式講述屬於臺灣的故事。「臺灣歷史和文化背景提供了如此豐沛的創作元素,而栢優座創團十年以來始終不變的理念,更是從這些元素中汲取養分,創造屬於臺灣的藝術、屬於臺灣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