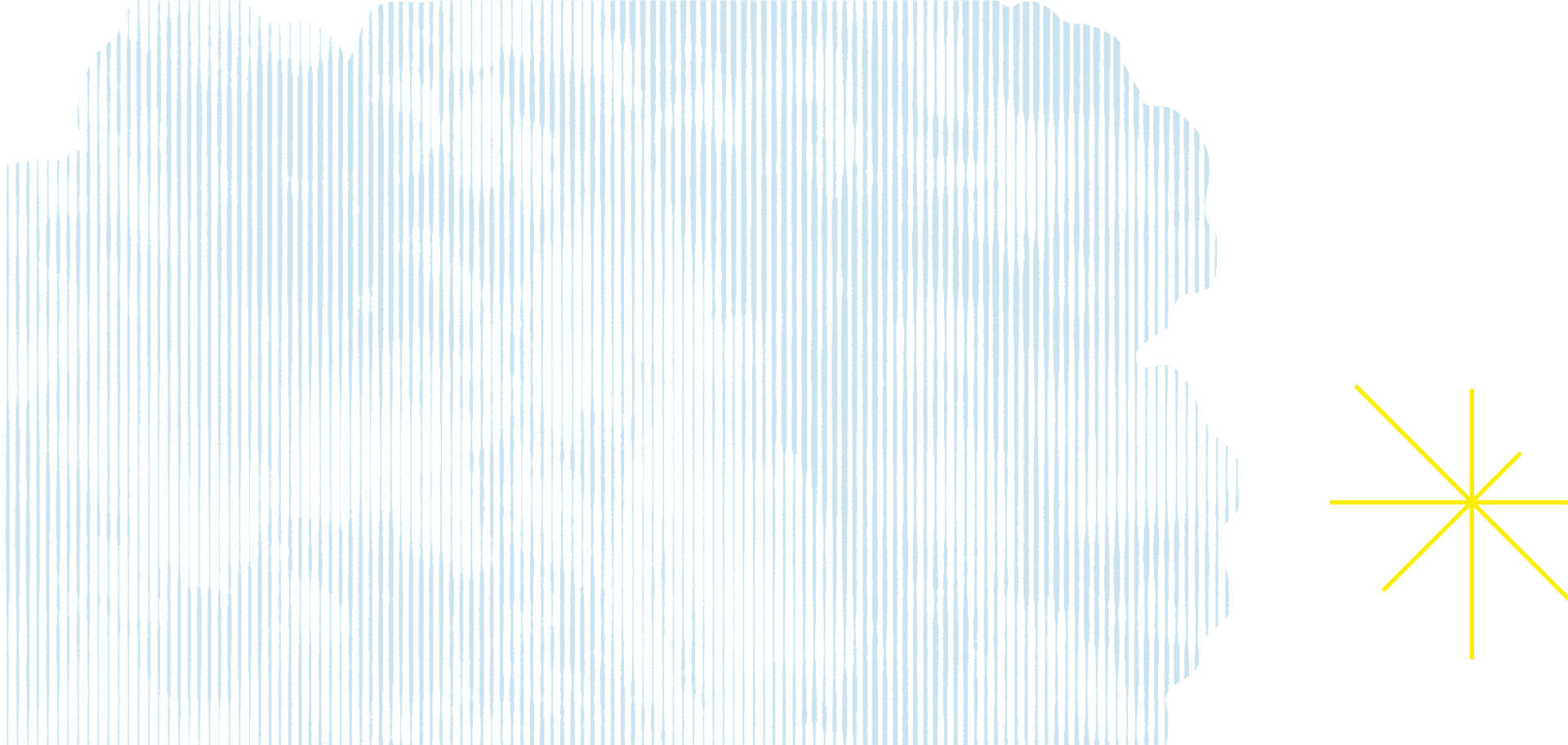部落格
2020.12.31
《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觀演心得:身而為人,.....?
時 間|2020年12月06日(日)14:30
地 點|臺藝表演廳
演 出|栢優座
撰 文|莊馥嘉(電影系四年級)
如同進入劇場前所預期的一般,《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始於東漢末年長板坡之戰一位鳴鼓人的死亡,以及靜置在他口袋中的「遺命牌」。
接著,「死神」渡鴉與擺渡人小渡進入鳴鼓金的視界,燈光由幽暗的森林群影、轉為溫馨的黃光,時空從東漢來到了現代,並聚焦在一個為除夕年夜飯張羅及煩惱的一家人身上。不一會兒,伴著鑼鼓聲響,報信人揮舞著旗幟進場,燈光一藍,時序再度回到了古代。隨著劇情的發展,前幾個我們能夠注意到的時序轉換的信號——包含投影背景的轉換、報信人的吆喝、「幕」與「幕」之間的過渡以熄滅所有的舞台燈光來達成——,都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甚至最後幾個過渡僅憑藍與黃光的調性切換,所有在舞台上運動的人們便瞬間切換了角色及身份。
.png) “何處是我家鄉?”
“何處是我家鄉?”
.JPG)
隨著時空的切換速度逐漸增快、直到近乎放棄了明顯的場面調度,我們便發現過去與當下已經慢慢地融合在一塊——在麋夫人與長媳各自的獨白中,她們之間的界線逐漸消失、差異逐漸消弭——最終我們看見的是,在古往今來的時間洪流裡,女人在中華傳統習俗的框架中所面對的問題是始終如一的。
麋夫人將強褓中的阿斗託付給趙雲的同時,訴說著自己對於「回到家鄉」的嚮往:「自從嫁給了劉備,我這一生都跟著劉備顛沛流離,每天都過得膽戰心驚......」麋夫人不願與趙雲回到劉備身邊,轉而來到井邊說道:「北方才是我的家鄉。」等在麋夫人面前的,或許是以自殺了結自己的性命,也或許回到北方的心願得了——麋夫人的命運尚未得到解答,時空便回到了現代。
除夕當夜,多年以工作為由、逃避回家吃年夜飯的三子,先是遇上了大嫂。大嫂叨念起自己的苦悶:「你知道你大哥,一直想要個孩子。其實我曾經拿掉了一個不是他的孩子。」當三子問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時,大嫂激動地說道:「難道要知道孩子是誰的,才構成離婚的理由嗎?」
再來,三子看見了四弟與四媳為了四弟的工作與兩人甫生下的孩子爭吵:四弟覆述著自己對於工作調派的無能為力,四媳則是責怪丈夫在家中長年缺席,在需要他時僅能獨自打理好一切。將長媳、四媳與先前麋夫人的絕望做對照,我們可以看到誕下子嗣以延續香火、組織並維繫家庭和睦的責任皆在古代及當代成為了限制女性追求自由及個體性的束縛。當四媳說「我不想要自己養小孩/一個人起床與睡覺。」時,不僅意味著孩子在懷孕的那一刻即注定成為女人一生的包袱,而沒有男人的情況下,她們更顯得無助。成為自由的女性,談何容易?
.png) “或許已是她,或許已是我”
“或許已是她,或許已是我”
作為三弟、趙雲及鳴鼓人,編導許栢昂在《大年初一》中的各個場景與時空之間來回穿梭,一下是勇猛的將軍趙子龍,轉眼又在現代成了逃避年夜飯的三子,偶爾也是為兒童講述故事的大哥哥。但若我們仔細探究,便會發現這些角色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甚至可以說這些角色在本質上皆是同一個人。
在《大年初一》的開場,這個「人」便已經死亡——更精確地說,已經被盜賊重傷到僅存一息——,而年夜飯的故事也是由這具遺體展開。的確,作為三子,這個人已然是幽靈般的存在:他鮮少回家過年,就連父親打電話給他時,也只聽見冰冷的「轉接語音信箱」。他的存在僅透過兄弟姊妹和父母的口述來確立,而我們也不見他的蹤影。對於大嫂和麋夫人而言,三子及趙雲的存在都是超然且旁觀的:他們總是不間斷地追著大嫂及麋夫人跑,無論如何都無法進入她們的內心,只能聽著女人從古延續至今、卻始終無以實現的對自由的想望。
然而,三子與趙雲無能理解女人困境的「困境」,與其單純地解讀成《大年初一》在敘事安排上的需要或是慣例,毋寧說是同時飾演兩個角色的導演,對於可對應到自身生命經驗的一種回應方式。這個旁觀的角色,是導演面對如此生命事件時的狀態:他無以理解的女人的困境,而現實中可對應到大嫂及麋夫人的人物,於他言也是難解的謎團。因此,當大嫂及麋夫人不約而同地說「你難道就只會叫我大嫂/夫人嗎?」時,也是導演回應生命經驗的方式之一:在前一個層面中,他試圖理解「嫁」一字對於女人的意涵,而後一個層面中,他也對於自己的不能理解感到無奈。「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走入婚姻。我只是想做我自己而已。」大嫂對三子所說的最後的一句話,或許是許栢昂面對生命中離自己而去的女性,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的理解了。
.png) 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
當我們先前在長媳及麋夫人身上,看見了生為女人在《大年初一》中的共通之處後,一人分飾兩角最終不再是必須關注的技術問題——演員方翊菲飾演長媳與麋夫人的同時,便是將女性在家庭中所面臨的問題集中於自身:她在古代是劉備的夫人,穿越了現代成為了與丈夫貌合神離的長媳。兩位女人借用了同是方翊菲的女性的身體,去表達了她們各自的愛恨情仇。
與方翊菲相同,許栢昂同樣是一人分飾三弟與趙雲兩角,但是隨著劇情發展,許栢昂在所有角色之間來回轉換的同時,也將自己困在敘事的迴圈裡:這個故事始於他的死亡,可卻只是第一層敘事而已。在三弟分別面對劇中的家人,並理解每個家人各有的苦衷後,鳴鼓金因為與盜賊搶奪鑼而被打死,渡鴉與小渡的再度出現將遺體與遺體之間的故事封閉成一個鏡框式的結構。而說故事的角色又於第一層敘事尚未結束之際,便開啟了新一層的敘事。
在鳴鼓金未了的心願明確了之後,一盞頂光打在許栢昂孤獨的身影上,他喃喃地說道:「他(鳴鼓金)應該已在另一個人生裡回家吃飯了。」隨後,許栢昂再度回到了三弟的角色中——在三弟為了逃避家人的爭吵而錯過了多年的除夕夜後,三弟今年終於在初一到來前偷偷地回了老家,只是家人都出門去了。正當我們以為三弟要在空蕩的家中守歲時,所有家人都回來了,包含那些同樣長年不願回家的親戚們。
不久前,許栢昂看似以旁觀者的身份,道出了鳴鼓人沒能回家與家人團圓的遺憾,然而筆者認為,比起旁觀者,許栢昂其後進入三弟角色的轉換過程,便是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鳴鼓金的遺憾及三子的躊躇上。此刻矗立於舞台中央的人,不再是三子、鳴鼓人或是趙雲,而是許栢昂自身——許栢昂透過自己所飾演的每個角色,試圖去彌補自己生命中未能完成的缺憾。在結局熱熱鬧鬧的年夜飯中,一個家庭團員了、《大年初一》圓滿落幕了,也滿足了觀眾對於一個完滿結局的期許與寄託,但是許栢昂想像中的家庭是否團員,我們終究不得而知。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栢優座《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彩排片段 攝影 游翔皓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栢優座《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彩排片段 攝影 游翔皓
或許,這樣溫暖的結局僅能存在於舞台上,如畫家江中澤曾在《自畫像》(The Last Painting, 2017) 中說道:「最美的事物,只能存在於畫框中。」生命的真相,在鳴鼓金身上得到了揭示——生命的本質,是充滿缺憾與痛苦的,但是,這同時是我們必須進入劇場觀賞戲劇的原因——它們提供了我們對於生活的某種想像,使我們的精神得以超脫與昇華。
地 點|臺藝表演廳
演 出|栢優座
撰 文|莊馥嘉(電影系四年級)
如同進入劇場前所預期的一般,《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始於東漢末年長板坡之戰一位鳴鼓人的死亡,以及靜置在他口袋中的「遺命牌」。
接著,「死神」渡鴉與擺渡人小渡進入鳴鼓金的視界,燈光由幽暗的森林群影、轉為溫馨的黃光,時空從東漢來到了現代,並聚焦在一個為除夕年夜飯張羅及煩惱的一家人身上。不一會兒,伴著鑼鼓聲響,報信人揮舞著旗幟進場,燈光一藍,時序再度回到了古代。隨著劇情的發展,前幾個我們能夠注意到的時序轉換的信號——包含投影背景的轉換、報信人的吆喝、「幕」與「幕」之間的過渡以熄滅所有的舞台燈光來達成——,都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甚至最後幾個過渡僅憑藍與黃光的調性切換,所有在舞台上運動的人們便瞬間切換了角色及身份。
.png) “何處是我家鄉?”
“何處是我家鄉?”.JPG)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栢優座《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彩排片段 攝影 游翔皓
隨著時空的切換速度逐漸增快、直到近乎放棄了明顯的場面調度,我們便發現過去與當下已經慢慢地融合在一塊——在麋夫人與長媳各自的獨白中,她們之間的界線逐漸消失、差異逐漸消弭——最終我們看見的是,在古往今來的時間洪流裡,女人在中華傳統習俗的框架中所面對的問題是始終如一的。
麋夫人將強褓中的阿斗託付給趙雲的同時,訴說著自己對於「回到家鄉」的嚮往:「自從嫁給了劉備,我這一生都跟著劉備顛沛流離,每天都過得膽戰心驚......」麋夫人不願與趙雲回到劉備身邊,轉而來到井邊說道:「北方才是我的家鄉。」等在麋夫人面前的,或許是以自殺了結自己的性命,也或許回到北方的心願得了——麋夫人的命運尚未得到解答,時空便回到了現代。
除夕當夜,多年以工作為由、逃避回家吃年夜飯的三子,先是遇上了大嫂。大嫂叨念起自己的苦悶:「你知道你大哥,一直想要個孩子。其實我曾經拿掉了一個不是他的孩子。」當三子問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時,大嫂激動地說道:「難道要知道孩子是誰的,才構成離婚的理由嗎?」
再來,三子看見了四弟與四媳為了四弟的工作與兩人甫生下的孩子爭吵:四弟覆述著自己對於工作調派的無能為力,四媳則是責怪丈夫在家中長年缺席,在需要他時僅能獨自打理好一切。將長媳、四媳與先前麋夫人的絕望做對照,我們可以看到誕下子嗣以延續香火、組織並維繫家庭和睦的責任皆在古代及當代成為了限制女性追求自由及個體性的束縛。當四媳說「我不想要自己養小孩/一個人起床與睡覺。」時,不僅意味著孩子在懷孕的那一刻即注定成為女人一生的包袱,而沒有男人的情況下,她們更顯得無助。成為自由的女性,談何容易?
.png) “或許已是她,或許已是我”
“或許已是她,或許已是我”作為三弟、趙雲及鳴鼓人,編導許栢昂在《大年初一》中的各個場景與時空之間來回穿梭,一下是勇猛的將軍趙子龍,轉眼又在現代成了逃避年夜飯的三子,偶爾也是為兒童講述故事的大哥哥。但若我們仔細探究,便會發現這些角色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甚至可以說這些角色在本質上皆是同一個人。
在《大年初一》的開場,這個「人」便已經死亡——更精確地說,已經被盜賊重傷到僅存一息——,而年夜飯的故事也是由這具遺體展開。的確,作為三子,這個人已然是幽靈般的存在:他鮮少回家過年,就連父親打電話給他時,也只聽見冰冷的「轉接語音信箱」。他的存在僅透過兄弟姊妹和父母的口述來確立,而我們也不見他的蹤影。對於大嫂和麋夫人而言,三子及趙雲的存在都是超然且旁觀的:他們總是不間斷地追著大嫂及麋夫人跑,無論如何都無法進入她們的內心,只能聽著女人從古延續至今、卻始終無以實現的對自由的想望。
然而,三子與趙雲無能理解女人困境的「困境」,與其單純地解讀成《大年初一》在敘事安排上的需要或是慣例,毋寧說是同時飾演兩個角色的導演,對於可對應到自身生命經驗的一種回應方式。這個旁觀的角色,是導演面對如此生命事件時的狀態:他無以理解的女人的困境,而現實中可對應到大嫂及麋夫人的人物,於他言也是難解的謎團。因此,當大嫂及麋夫人不約而同地說「你難道就只會叫我大嫂/夫人嗎?」時,也是導演回應生命經驗的方式之一:在前一個層面中,他試圖理解「嫁」一字對於女人的意涵,而後一個層面中,他也對於自己的不能理解感到無奈。「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走入婚姻。我只是想做我自己而已。」大嫂對三子所說的最後的一句話,或許是許栢昂面對生命中離自己而去的女性,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的理解了。
.png) 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當我們先前在長媳及麋夫人身上,看見了生為女人在《大年初一》中的共通之處後,一人分飾兩角最終不再是必須關注的技術問題——演員方翊菲飾演長媳與麋夫人的同時,便是將女性在家庭中所面臨的問題集中於自身:她在古代是劉備的夫人,穿越了現代成為了與丈夫貌合神離的長媳。兩位女人借用了同是方翊菲的女性的身體,去表達了她們各自的愛恨情仇。
與方翊菲相同,許栢昂同樣是一人分飾三弟與趙雲兩角,但是隨著劇情發展,許栢昂在所有角色之間來回轉換的同時,也將自己困在敘事的迴圈裡:這個故事始於他的死亡,可卻只是第一層敘事而已。在三弟分別面對劇中的家人,並理解每個家人各有的苦衷後,鳴鼓金因為與盜賊搶奪鑼而被打死,渡鴉與小渡的再度出現將遺體與遺體之間的故事封閉成一個鏡框式的結構。而說故事的角色又於第一層敘事尚未結束之際,便開啟了新一層的敘事。
在鳴鼓金未了的心願明確了之後,一盞頂光打在許栢昂孤獨的身影上,他喃喃地說道:「他(鳴鼓金)應該已在另一個人生裡回家吃飯了。」隨後,許栢昂再度回到了三弟的角色中——在三弟為了逃避家人的爭吵而錯過了多年的除夕夜後,三弟今年終於在初一到來前偷偷地回了老家,只是家人都出門去了。正當我們以為三弟要在空蕩的家中守歲時,所有家人都回來了,包含那些同樣長年不願回家的親戚們。
不久前,許栢昂看似以旁觀者的身份,道出了鳴鼓人沒能回家與家人團圓的遺憾,然而筆者認為,比起旁觀者,許栢昂其後進入三弟角色的轉換過程,便是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鳴鼓金的遺憾及三子的躊躇上。此刻矗立於舞台中央的人,不再是三子、鳴鼓人或是趙雲,而是許栢昂自身——許栢昂透過自己所飾演的每個角色,試圖去彌補自己生命中未能完成的缺憾。在結局熱熱鬧鬧的年夜飯中,一個家庭團員了、《大年初一》圓滿落幕了,也滿足了觀眾對於一個完滿結局的期許與寄託,但是許栢昂想像中的家庭是否團員,我們終究不得而知。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栢優座《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彩排片段 攝影 游翔皓
大觀國際表演藝術節-栢優座《大年初一前晚的那頓飯》彩排片段 攝影 游翔皓或許,這樣溫暖的結局僅能存在於舞台上,如畫家江中澤曾在《自畫像》(The Last Painting, 2017) 中說道:「最美的事物,只能存在於畫框中。」生命的真相,在鳴鼓金身上得到了揭示——生命的本質,是充滿缺憾與痛苦的,但是,這同時是我們必須進入劇場觀賞戲劇的原因——它們提供了我們對於生活的某種想像,使我們的精神得以超脫與昇華。